 |
| 20世纪50年代,舒同与家人合影(左起关关、安安、舒同、均均、舒同夫人)。 |
口述:舒均均 整理:程诉
舒同:(1905-1998年),江西东乡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长征中,任红二师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社会部部长等职。
舒均均:1947年出生。1966年毕业于北京舞蹈学校。现为中央芭蕾舞团国家一级编导,文化部艺术节文华大奖四届评委,中国舞协会员。
解放后,有一股为全国的报刊题字的风潮。毛泽东和舒同成为最大的出品人。那时候,华东地区的各个报刊想请毛主席题字,可毛泽东说“你们山东有个大书法家,舒同啊”。有了毛主席的这句话,华东地区的题字就都落到了父亲手里。有人戏称,中国的报纸是两分天下,一半是毛泽东,一半是舒同。
父亲曾被内定为“台湾省委第一书记”
建国之初,父亲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主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校长、中共华东局党校校长,又兼任《解放日报》的工作。父亲不仅是身兼六职,办公地点还在两个不同的城市。华东局的工作在南京,解放日报的工作在上海,父亲就在南京和上海之间来回跑,工作繁忙程度可想而知。我们小时候,整天都见不到父亲,只知道他成天到晚就是忙工作,根本没时间和我们在一起。
那时,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刚刚解放,工作千头万绪。父亲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早上又很早就起来工作。不过,父亲无论怎样的忙,也没有看到他着急。他总是那么平和,总是微笑着细声细语地说话,从不发脾气。
由于工作的繁忙,父亲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有限的几个小时休息时间还常常无法入睡。整天睡不着觉,导致父亲经常头疼,有时候疼得受不了,他就用头往墙上撞。医生也没有办法,为了缓解头疼只好给他弄了一个铁做的头箍,疼的时候就套上,来缓解症状,父亲说,就像戴了个紧箍咒。每当父亲头疼的时候,母亲就抱住父亲的头,给他按摩。
由于长时间坐着办公,父亲还患上了严重的痔疮,一坐下就疼得受不了。我记得,父亲为了能正常工作,弄一个小游泳圈,每天坐在上面来缓解疼痛,坚持工作。父亲忘我工作了一年多,终于病倒了,在医生强迫下,父亲才住院修养。
从医院出来后,父亲来到杭州修养了一段时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第一次休假,这次休假原本是不带孩子的,可是下面工作人员提议把孩子们接过来助兴。我记得父亲陪着我们在杭州西湖边上散步,有说有笑。可惜的是我们几个孩子要上学,也就呆了两三天。
我听说,中央曾经内定父亲做台湾省委的第一书记,主要是看重了他是知识分子,有文化、文采好、又是知名的书法家,又做过敌工部长,到了台湾之后可以更好地做统战工作。早在1936年,父亲就有统战工作的经历。当时,红军到达陕北边区政府管辖的旬邑县时,为团结抗战,边区政府拟请当地一位前清翰林出任参议员。那位老夫子说,“我和没文化的人谈不来”。毛泽东知道后,就让舒同以中央名义给他写一封信。这位前清遗老读信后连声称服:“字美文雅,想不到共产党内也有人才啊!”随即出山。
可是由于解放台湾的事情一拖再拖,父亲就没当上这个内定的台湾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组织上征求父亲的意见,叫他在人民日报社长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两个职务中选一个,父亲考虑自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多年在山东工作,对山东的老百姓很有感情,加之他长期做宣传工作,都是配合别人工作,自己很想到地方上工作,当一把手。于是父亲毅然选择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工作。
“粮食亩产3000斤”,上上下下都说假话
1954年,父亲被调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开始第一次全面抓一个省的工作。他精神抖擞,工作上干劲十足。那时候家里的条件比较好,住在一个独门独院的房子,有厨师、保姆、警卫员,我们这些孩子也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开始的时候父亲在山东干得不错,这期间毛泽东曾六下山东,足见主席对父亲的赏识,并且毛泽东常拿山东做自己的试验田。1959年,巴西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普列斯特斯和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夏基等一行来济南参观访问。在济期间,毛泽东分别会见了他们。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夏基说,“我们是知识分子,不搞武装斗争,我们搞议会斗争”,毛泽东笑着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也有知识分子,他指着父亲说;“我领导一个国家,他领导一个省”,父亲听了不免受宠若惊。
由于山东各方面形势都很不错,父亲的头脑开始发热。父亲这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在颜真卿曾经出任平原太守的地方,干出一番大事业!这时候,大跃进运动开始了,父亲是知识分子出身,不懂农业,他一门心思、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精神,很多事明明知道有困难,还无条件做。下面的人为了逢迎都不敢讲真话了。
1958年8月17日,北戴河会议上,中央决定发动人民公社运动,当时,父亲心里很复杂,一方面各地报告的粮食增产巨大,另一方面征购任务却完不成,农副产品供应紧张,城市中出现了要饭的人。母亲回忆,这个时候父亲对她说:“来到山东工作4年了,任务一件接一件,比过去打仗还紧张,过去打完一仗总有个休整的时间,现在几乎是忙的没有喘口气的时间。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这个刚刚完成,下一个就来了,我的脑筋总是绷得很紧很紧,有时候像要炸裂似得头疼。1956年是三大改造,1957年又是反右斗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1958年就是大跃进……”
1959年6月,为了解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父亲决定下生产队当社员,我们一家人都跟着去了农村,父亲带着我们参加收割,住在农家院子,吃的农家菜炒鸡蛋、玉米饼什么的,现在想想,肯定是受到了优待,真正的农民吃不上这样好的饭菜。父亲说:“我要亲自收一亩麦子过过秤,看能产多少粮!”,他亲自收了一亩麦田,这一亩地算出来竟产出了3000多斤粮食,父亲很高兴,觉得这下可是掌握了实际情况了,可他不知道自己被骗了——下面的人在脱粒机里预先装了2000多斤粮食!父亲是知识分子出身,并非农业上的行家里手,也就被蒙了过去。
这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打倒,本来想开始纠左的父亲又紧跟中央指示,参与到了反右斗争中去。这一年,山东省按“浮夸风”的高标准征调粮食,农民根本交不出,即便把种子都交上去也不够,有的人家把谷仓里最后的谷子交上去之后,全家上吊自杀了。这件事震动了中央,经过调查,1960年10月,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代表中央宣布撤销父亲的职务。
当时父亲还是中央委员,来北京开八届九中全会,有一天上午我就去看父亲,我们到了北海公园,那天父亲顶着风走,走得特别快。我在后面跟着,叫他“爸爸,你别走这么快,我都跟不上你了”,父亲回过身来说:“爸爸被人骗了”,刹那间留下了眼泪。为了安慰他,我唱起了他最喜欢唱的“力拔山兮气盖世”,从前父亲只唱这第一句,这一次父亲给我唱了后面的三句:“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四清运动”得罪老战友胡耀邦
父亲被撤职后不久便恢复了工作,当了一段县委书记,后来组织上也觉得对他的处理过重了,“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中央承担了主要责任。这样父亲便又回到了省委书记的岗位上。这一次,父亲被调到陕西,分管文化、宣传。在陕西时,父亲曾对我说:“我被人骗了,上上下下都在说假话,我对不起山东人民。”
胡耀邦1965年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父亲在陕西是省委副书记,两个老战友又走到了一起。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父亲就和胡耀邦关系很好。1940年,父亲率晋察冀代表团赴延安开会,由于七大延期,他便留下来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则是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整风运动中,他俩都是整风运动领导小组副组长。两个人住的窑洞很近,又都是江西老表,于是经常走动,见面亲热得很,称兄道弟,你给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有时候,胡耀邦来找父亲,母亲一定会从院子里摘两个自己种的西红柿,拌酱油辣子当菜,再来点花生米,两个人吃着喝着聊一个晚上。
胡耀邦对父亲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对陕西省的人说:“舒同是老同志,不要把他当一般的副书记看,我是什么待遇他就应是什么待遇。”在胡耀邦心里,父亲的资历比他老,又是由于执行中央的命令而犯错误,很同情父亲,也很照顾他。胡耀邦刚到陕西的时候,家人还没有来,于是他常常星期天到我家来吃饭。
西北局在“四清运动”中比较“左”。在陕西主政的胡耀邦发现了“左”的问题,立即予以纠正,并向西北局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西北局的领导和新来的胡耀邦就有了点矛盾。在这个问题上,父亲支持了西北局的观点,这是胡耀邦所万万没有想到的,感到痛心疾首,说出了“你不够朋友”的话。在运动的压力下,胡耀邦身心疲惫,突发脑炎病倒了。现在看来当然是父亲不对,但父亲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时候都说“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父亲深受这句话的影响,宁左勿右。
毛泽东支持了西北局的意见说:“胡耀邦要是不革命,就叫他走嘛!”恰好叶剑英来陕西视察工作,看到胡耀邦很受气,就把胡耀邦调回北京工作了。父亲紧跟西北局,得罪了胡耀邦。临走时父亲去送胡耀邦,主动与他握手,被胡耀邦拒绝了。
“文革”中被批斗知道自己当权时整错了人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父亲和陕西省的一些领导一起都靠边站了。“文革”初期父亲被陕西的造反派关押,待遇还好。虽然有批斗,但还没有打人的。巧的是,胡耀邦被拉回陕西,在斗争大会上和父亲一起挨批斗。两个老战友又一次互相照顾,父亲说,胡耀邦在自己挨批斗时还说:“快去照顾一下舒同,舒同年纪大了,都站不稳了。”那一刻,父亲心里知道,耀邦已经原谅他了。1967年夏天,山东的造反派拿着革委会的介绍信,点名要父亲去山东挨斗,接受山东人民的斗争。父亲主政山东期间,在“反右运动”中也犯了“左”的毛病,许多人被错打成右派,还有人被开除党籍;大跃进的时候父亲在山东也整过一批人,这些人在文革中有的成了造反派,他们心里有气,便翻旧账,把父亲从陕西揪回山东,批斗了好几个月。当得知父亲被山东的造反派带走后,弟弟舒安马上跟去保护、送去衣服,并向中央文革递了材料。当时,纪登奎说了一句“舒同还是到陕西接受批斗吧,你们山东就不用管了”。父亲才得以回到陕西。
回来后父亲心情很沉重,不是因为有人打他,而是他知道,在他当权时确实整错了人,“反右”斗争把人家搞得很惨。大跃进之后,对自己“左”的问题曾有过反思,可在“文革”遭批斗时,那些群众跟他对质,他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导致的后果。有的人一生的前途就毁了;有的人因为错划成右派而自杀。说到激烈处,一个红卫兵一拳把父亲打倒在地。
回到陕西后,父亲被军管了,虽然待遇上很糟,但是客观上起了保护的作用,起码不会再挨打了。专案组抓住父亲的历史问题不放,非要叫他承认自己是“间谍”。父亲的历史问题确实有一点小瑕疵。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父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被迫在国民党的军校隐蔽下来,寻找党的消息。后来他在报纸上了解到江西剿共的情况便立刻去投奔,刚到苏区的时候正赶上肃反杀AB团,父亲不敢说自己这段历史,讲了就是死。
到了延安之后,他曾经和胡耀邦汇报过自己在国民党军校的情况。“文革”中,这段历史就成了问题。父亲不认账,跟专案组死顶。后来专案组退了几步,答应说可以不算你叛变,可起码算脱党啊!你只要同意减少两年党龄就放你出来。可是就这个父亲也不承认!他说:“就是把牢底坐穿也不承认自己有脱党问题。”
胡耀邦告诉我:父亲的问题快解决了
“九一三事件”之后,政策有了松动,胡耀邦也已经解放,正在等待分配工作。这时,胡耀邦的住所几乎成了老同志和老同志子女的联络站了。经常有很多人来听听形势啊,找他递些材料。早听母亲说,父亲和胡耀邦的关系好,为父亲的事情,我也找过耀邦叔叔。那时候胡耀邦家里是门庭若市,反映情况的人很多,耀邦叔叔知道我来了,叫我等他15分钟,等他把这一拨人送走,单独和我谈谈。我当时看到人很多,不知道何时才能见到耀邦叔叔,等了一会儿我就回去了。回到西安后,我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信的内容有两个,一方面是问问父亲的情况,看看何时能解放?并对西北局时两人的矛盾,代父亲表示歉意。另一方面是我自己对国家前途表示深深的担忧。没过多久胡耀邦就回信了。
1972年,父亲终于解放了。后来,父亲到北京来申诉,我陪着他一起看胡耀邦叔叔,这时候,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到,胡耀邦叔叔也跟着被打倒了。在协和医院父亲见到了卧病在床的胡耀邦,他笑着说“我现在又被打倒了”,父亲笑答,“没有关系,会好起来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父亲在1979年9月得以恢复名誉。这时父亲又去找时任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他希望能回到部队。胡耀邦先安排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后来到军事科学院当副院长,并主持撤销了父亲在山东受的处分。晚年的父亲安享家庭生活,从一个政治人物回归为一位书法家。他的书法也逐渐走到了行书艺术的最高峰。今天定型在电脑中的“舒体”圆润、内敛,与他早年的作品已大不相同。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使父亲的性格变化很大,反应在书法作品上就是“藏锋”二字。
采访结束时,舒均均说,我仔细回想,建国后舒同任山东省省委书记,又在陕西省和军事科学院任职,可大家还记得他是一位书法家。他被誉为“红军书法家、党内一枝笔”,被毛泽东戏称他为“马背上的书法家”,被何香凝女士称为:“国共有两支笔,国民党有于右任,共产党有舒同”。百年之后,人们可能忘记父亲所有的职务,但不会忘记他的书法。因为他的书法称为“舒体”,这种字体已经进入了全世界所有电脑的中文字库,成为记录历史文化的工具,成为不可磨灭的印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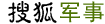








 动物系恋人啊 | 钟欣潼体验爱情哲学
动物系恋人啊 | 钟欣潼体验爱情哲学 南方有乔木 | “科创CP”渐入佳境
南方有乔木 | “科创CP”渐入佳境 魔都风云 | 周冬雨任达华演父女
魔都风云 | 周冬雨任达华演父女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